|
|
「 秋風清,秋月明;落葉還聚散,寒鴉栖復驚。相思相見知何日,此時此夜難為情。」
睡夢中又是一陣心悸,將我拉回現世,久久不能自己。
唉,這傢伙,咱們分開該已有十年之久了吧?
不過應該將近三年沒想到你,沒夢過你了。
昨晚與幾個朋友到一家PUB飲酒閒聊,裡頭駐唱的樂團倒是令人眼睛一亮,很
久沒聽到專唱純搖滾樂的團。
呵,搖滾樂嗎?我只知道現在到處充斥著所謂的電音,以及搖頭舞曲。
於是我停下與朋友的攀談,專心聆聽著臺上樂團的演唱。
閉上眼,彷彿EAGLES,DEEP PURPLE,QUEEN,SCORPION,VAN HELEN,
逐一回到我的身邊,那個屬於搖滾樂的年代,如此遙不可及的過往,復又歷歷在
眼前。
「 這是什麼鬼啊?重金屬音樂?快要把人吵死了!」
聽到鄰桌有人這樣抱怨著,我先是冷笑,然後苦笑。
舞臺上這個我不知名稱的樂團,才剛以一首JUMP讓現場熱絡到最高點,接著便
沉寂了下來,五光十色的旋轉燈也跟著黯淡,只餘下一盞昏黃微弱的燈光正照在
抱著吉他的主唱身上。
全場寂靜下,他輕輕撥起和弦,然後跟著響起了SOLO。
我開始驚疑不定,正隨著這熟悉卻似陌生的樂曲心蕩神馳之際,主唱搖頭晃腦地
,跟著和弦吹起了口哨。
「 喂喂,是槍與玫瑰的『耐心』耶。」
身旁友人猛拍我的肩膀說著:「 好久沒聽到這條歌啦。」
他一連拍晃著,卻見我毫無反應,遂伸長脖子到我眼前來。
才知我早已淚流滿面。
PATIENCE,年輕時怎樣也記不住這個單字,所以叫這首歌為『耐心』。
就是這一條PATIENCE,才讓我又再想起你這可惡的浪子。
阿耀。
那是我生平打過最不爽快的一場架。
才剛開打,便被一堆同學夾頭夾腦地架開,那傢伙明擺著打不過我,嘴上粗話還
兀自罵個不休。
這年我才國二。我橫行霸道,他憤世嫉俗。
自從他上學期轉學到我們班上,我就怎麼看他都不順眼。
瘦弱的身軀,蒼白的臉龐,卻吊著一雙陰騭凶狠的眼睛。我懷疑他從來不懂用正眼看人,只會斜瞪惡視。
也忘了是如何跟他打起來的,只記得我和他後來就在教室門口罰站。
教室裡頭仍舊在上課,我們並肩站著。
「 他媽的,算你運氣好。」 我冷冷說道:「 要不是同學拉得快,我肯定會把你打死,瘦皮猴。」
他斜著眼睛瞪來,冷哼一聲,惡狠狠地說:「 你體格好是沒錯,但要把我打死之前,我會先砸爛你的頭。」
「 別光只會出張嘴巴。」
「 來啊,要不要試試?」
於是第二場架又再度開打。
我們的導師也很寶,下課後就把他的座位調到我隔壁來,要我們相親相愛。
我的日子開始難過起來。
這傢伙根本沒有半個朋友,生性孤僻乖戾,所有人都對他敬而遠之,而我則是他的頭號死對頭,卻一天有九個小時要坐在一起,其精采可想而知。
反正動不動就會打起來,不知打過多少次架了。
有時明明沒事,他便斜眼瞪來,罵了一聲雜碎,我自然一拳砸過去。
有時我閒著無聊,就愛去伸腳踹他的椅子,他當然立刻撲過來。
打架打到所有人都懶得勸解了,早已見怪不怪。
是一個炙陽灼灼的慵懶下午,我趴在課桌上正悶著,本想再伸腳去踹他兩下桌腳,卻見他斜倚在窗邊,怔怔望著藍天。從沒見他的眼神如此溫和過,忍不住開口問:「 嗯?你在看什麼鬼?」
他轉過頭來,眼神復又變得冷傲孤僻,哼地一聲回答我:「 干你個屁事啊?我今天不想跟你鬥,別來惹我喔。」
不知怎地,我竟沒對他說的話發脾氣,只覺得突然興致勃勃想逗弄他,又問:「 你不覺得自己很怪嗎?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欠了你似的,都對不起你,都跟你有仇,要不然你幹什麼一天到晚就一副死人臉?」
「 我操。」 他狠狠瞪視著我,我們一如往常的互瞪。
他竟長長嘆了一聲,像顆洩了氣的皮球般,又斜靠著窗邊。
「 你們這種好命的小孩,什麼都不懂的啦。」 他似笑非笑地說。
當時的我年少氣盛,最看不過人家用倚老賣老的口氣跟我說話,還說我什麼都不懂,被這麼一激,我決定去探查他的底細背景。
我詢問過導師,問過訓導處教務處,也問了常對他諮詢的心理輔導老師。
豈知每問過一個人,我的心裡便涼了一截。
原來他的母親早亡,父親續了弦後又病逝了,只留下他和繼母,及一個同父異母的弟弟相依為命。
既不干父系也不干母系,因此所有的親戚朋友對他們完全不聞不問,繼母的情況更糟,不但酗酒賭博,更患有輕微的精神疾病。
繼母平常或心情好時,大家都相安無事,要是喝了酒賭輸錢或精神狀態不穩定,便是換來一頓毒打。有時還會突然發起癲來,丟下他和弟弟,一跑出門就是好幾天不回家。
他們一家完全沒有收入,只靠政府的些微補助在過活。聽說他轉來我們學校還是因為躲債搬家,學費是以前的老師張羅來的。
我突然極度厭憎自己。
我從來不知道自己這麼可惡,竟糟蹋這樣一個可憐的孩子,同時也才理解原來他的憤世嫉俗其來有自。
「 喂喂,最近轉性啦?還是知道害怕了,不敢來惹我?」
有一天他突然踢我的椅子,如此對我說著。
自從得知他的背景,也不明白是內疚或者同情,早已不再和他鬥氣爭吵;望著他帶挑釁的表情,只是笑笑地說:「 算了吧,哪來這麼多架好打?我雖然不愛唸書,可以沒想過以後要當流氓。」
「 哈,吃錯藥啦?」 他也笑了,空洞的眼神似乎不再那麼惡狠。
「 那你以後想做什麼?」他問。
我雙手一攤:「 小時候說要當總統,當太空人,現在想要當麥克傑克遜,他真是夠屌的。」
「 麥克傑克遜?就憑你?你會他摸老二抖腰那一招嗎?」
我們同時哈哈大笑,兩人所有的恩怨至此煙消雲散。
那天彼此一聊開,話就多了,原本就不想再跟他吵架,但和好的原因我從沒有說,我明白他驕傲得緊,自尊心遠比一般人強得多,便裝作什麼都不知道,把這個秘密永遠埋在心底深處。
結果跟他成了好朋友,唯一的朋友。
阿耀不愛唸書,不愛與人說話,都是出了名的;即使是與唯一有交情的我,一天也說不上幾句話。
有一次我突然問他,既然在學校沒有可以聊的人,回到家會跟繼母或弟弟聊嗎?
「 吉他。」 他聳聳肩,淡淡說道:「 我只跟吉他說話。」
我怔了一下,隨即感受到他心底的寂寞。
「 不信是嗎?不然放學以後到我家來坐坐。」 他說。
我猜他一定從沒帶過朋友回家,從他繼母臉上表情可以十分確定。
他帶我進了房間,僅可容納一張床舖的斗室,門一甩,珍而重之地將一把鋼弦吉他抱在懷裡。
「 這叫民謠吉他,柄上有十六琴格的。」 他一手又指著牆角另一把深色紋路的吉他,說著:「 那是古典吉他,十四琴格,尼龍弦。」
我擺一擺\手,打斷他的話:「 知道啦,我也學過好不好?」
「 你有學過啊?那好得很,彈來聽聽看。」 他眼睛發著光,把懷裡的吉他遞過來給我。
那時我算是學過一陣子,雖然只會些粗淺的和弦與指法,但也能自談自唱搞定一首歌,稱得上志得意滿。
C∼Am∼Dm∼G7, 四個和弦就能唱「歡樂年華」,「恰似你的溫柔」,還有好幾首校園民歌,史稱無敵四和弦。
他聽我叮叮噹噹地用這招連唱三條歌,突然一把將吉他給搶了過去,罵道:「 夠了吧,你只會這些對吧?」
「 對啊,還沒聽說過同年紀有人比我厲害的。」 我傲慢地斜仰著頭。
「 去你的。」 他笑罵著:「 你這款調調的喔,擺明就只是要學會自談自唱好把馬子就行了,沒半點長進。」
我當然不認輸,直瞪著他。
他哼聲說道:「 不服氣啊?閉鎖和弦會不會?單音SOLO會不會?古典指法?滑音?BASS?」
說了一串聽不懂的,只好邊搖頭邊瞪著他。
阿耀淡淡一笑,是我從沒見過的神氣。
他翹起了腿,輕輕撥動了琴弦,同時優美動人的旋律在耳畔舞了起來。
我記得那是電視上某個廣告的配樂,就像原音重現般。
餘音未歇,又響起了澎湃激揚的樂音及節奏,聽得令人熱血沸騰,後來我才知道那就是搖滾樂。
也不記得他彈奏過多少種多少首,只覺得千變萬化引人入勝,目眩神馳的同時也已如癡如醉。
我開始明白他所謂和吉他說話是怎麼回事了。
原來那跟寂寞是完全扯不上關係的。
還以為他與一些所謂自閉兒一樣,在外頭鬱鬱無言,回到家中關上房門,便孤伶伶地同洋娃娃說話,同牆壁聊天。
我看著他神聖而不可侵的表情,聽著他釋放出來的音樂能量,這才深深明白,其實他是只肯與吉他真心對談。
阿耀這時就像完全換成另一個人似地,閃爍著光芒,我所認識熟悉的,那個陰騭凶狠憤世嫉俗蠻不在乎的小子,竟不見了。
最後一個尾音拉得極長,繞樑緩緩而止,他又恢復了那個鬼樣子,似笑非笑地看著我。
「 服了沒?我可以收你當徒弟喔。」 他說。
我心裡早已嘆服,只是臉還拉不下來,兀自語帶不屑說著:「 你厲害,教你的當然更厲害,我要跟你師父學去。」
他哈哈大笑,搖頭說:「 哪有什麼人教我,我都看書上寫的,再自己去慢慢摸索出來。」
「 怎麼可能嘛?」 我反駁他:「 我也有看書啊,怎麼就看不懂,那些王八綠豆的音符節拍五線譜你都懂嗎?我才不信。」
阿耀回答:「 我也不瞭囉,看不懂就跳過去啊,講樂理我就十足是個白癡,反正六條弦十六格,再怎麼變一定還是能抓到那個音的啦。」
「 樂理你完全不懂?又能玩吉他玩成這樣?」 我傻住了。
「 我是天才嘛。」
他笑得好燦爛。
我開始跟阿耀學著玩吉他,又拉了另一個死黨大胖,每天放學就到阿耀家裡報到。
房門一鎖,小房間就是我們的天下。
我們在小房間裡嘶吼,狂鬧,飆歌,似是要把所有不知名的愁緒以及沒來由的抑鬱盡數發洩出來。
阿耀的繼母總是皺著眉頭,但至少阿耀不再對她挑釁頂嘴,也就懶得來管我們,依舊打她的牌喝她的酒。
而我們除了玩吉他,也時常帶一些音樂錄影帶到阿耀家裡看,大胖家開的是錄影帶出租店,帶子總是把書包塞得滿滿。
有時看到亢奮處,我們總是又叫又跳。
「 喔喔,平克佛洛伊德,THE WALL!」
「 我的天哪,KISS實在太勁爆了!」
「 哇!瑞克史賓菲爾德,你看他吉他飆成這樣!」
阿耀,大胖和我三個抱在一起,簡直快瘋了。
這時我們開始接觸搖滾樂。
只是這樣的日子並沒能持續多久。
國三上學期末,某天阿耀突然說,他恐怕要休學了。因為他的繼母在外頭又再滾了一屁股債務,已被逼得走投無路,看來又要搬到很遠的地方去躲債。
分離在即,我和大胖硬逼著他答應,無論人在何方,一定要和我們保持聯繫。
我們說好了以後要一起玩音樂的。
他來學校辦休學那天,把他最心愛的鋼弦吉他帶來說要送我,我堅持不肯收他的寶貝,他翻臉了。
還是大胖替我收下的。
阿耀穿著便服,斜倚在窗邊,將叼在嘴角的萬寶路香煙點著火,冷冷望向桌上,我和大胖幫他整理好的課本作業雜物。
「 幹!這些還留著幹什麼?老子以後不唸書啦!」 他一腳將桌子踹翻,大聲咆哮。
一陣脾氣發完,轉過頭來對我相視苦笑。
我緊緊抓住他的肩膀,咬著牙說:「 你這個渾球,要麼回來教會我彈吉他,要麼回來再跟我打一場架。」
阿耀點頭說:「 他媽的,我會回來找你們,一起開場暴力演唱會。」
然後他雙手插口袋,吊兒郎當地走出校園。
卻再沒和我們聯絡了。 |
|
|
|
|
|
|
|
|
|
|
|

樓主 |
發表於 2006-8-1 15:11:38
|
顯示全部樓層
十年的時間,用十根手指頭便能數完。
天知道是多長遠多難熬的一段日子?
在外島服兵役,兩年間只回台灣兩次;軍旅生涯儘陪伴著我的,白晝是藍晃晃的海,夜晚是數不清的星。
當兵彷彿把人給當傻了,我變得寡言自閉,陰沉憂鬱。
變成孤獨一個人。
退伍後的幾年間,想必也因自己這般灰暗性格,使得工作,家庭,感情,人際關係樣樣失敗,極度不得志。
我離群索居,在中興橋邊租了一間兩坪大的小套房,除了上班吃飯睡覺,便是躺在塌塌米上抽煙發呆,癡愣愣地望著天花板。
有時喝多了酒,任憑怎麼想也想不出該繼續活下去的理由時,會開始發起酒瘋,不停地傷害自己。
那是我一生中最糟的一段日子,拖著空蕩的軀殼過著渾渾噩噩的生活。
有一天在回家路上,不經意遇見一個國中同學,向來都不熟的那種。
寒暄了幾句,他說大胖一直在找我,並給了我他的電話號碼。
回到家中,我足足猶豫掙扎了數天,心想是否該與大胖聯絡;畢竟國中時代除了阿耀,大胖算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但另一方面又自覺形慚,幾次拿起電話筒,號碼硬是撥不下去。
某晚多喝了點酒,終於狠下心撥電話給他。
和大胖十餘年不曾聯絡,彼此聽到好友的聲音,忍不住異常歡喜的情緒,一整晚都在互道別來情衷。
第二天下班,我就像無主孤魂在街上漫無目的地晃著,直到晚上九點半,才到雙城街裡的一家小PUB,與約好的大胖在那兒碰面。
久違的老朋友見面自然興奮莫名,大胖沒什麼太大改變,只是更大了一號,穿著上也人模人樣得多,說起話來照舊是霹哩趴啦一整串珠連而來。
看他那副模樣,心底不由得湧起一陣暖意。
我們坐在吧檯喝酒聊天,聽著舞台上的樂團演唱著BON JOVI 的BED OF ROSES;這個團的整體素質都還算在水準以上,只可惜主唱的唱功差了一點,和原唱者的味道相去甚遠。
我自己也是愛唱歌的,或許我的標準嚴苛了點。
「 這個BAND唱得如何?」 大胖這麼問著。我便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。
大胖笑了笑,又問:「 你呢?還有在玩吉他嗎?」
我搖搖頭,苦笑說:「 早就沒了,現在連騙小孩都不成。」
這時台上的樂團唱完最後一首歌,正在收拾樂譜樂器,一個長髮披肩的削瘦男子朝我們走來,與大胖寒暄。我記得他是樂團的吉他手。
「 來來來,跟你介紹一下。」 大胖拍拍我的肩膀,眼底盡是笑意。
那長髮男子用手肘頂了大胖兩下,罵道:「 神經病,介紹個鳥啦!」
他撥開長髮,迎面對我笑著說:「 阿文,媽的連老朋友也認不得喔?」
耳畔的聲音是如此熟悉,我吃驚地緊盯著這個男人。
捲長髮,骷髏頭背心,長釘腰帶,破牛仔褲,半統馬靴;這些都不曾有過印象,但蒼白的臉色,削瘦的臉龐,高挺的鼻子,薄窄的嘴唇,再配上那雙憤世嫉俗且不可一世的眼睛,卻是熟得不能再熟了。
「 阿耀?」 我下意識一拳便搥在他的胸膛:「 去你的,你還活著啊?」
他揉著胸口微笑:「 你還真他媽的難找呢。」
也不知是興奮或激動,我們抱在一起,還有大胖。
十年了。
整整過了十年,我們三個又再抱在一起。
燈光,音樂,威士忌;伴著我們互道這些年來的日子,有笑有淚。阿耀聽說我再沒碰過吉他,顯得訝異萬分。
「 你還真糟糕耶。」 阿耀指著我的鼻子罵道:「 看你這副鬼樣子,靠,我是不是認錯人啦?」
「 唉,就一個字,悶。」 我嘆氣道。
阿耀頻頻勸酒,大胖溫言安慰,沒過多久,三個人都有點醉意了。
大胖突然說:「 阿文,你以前英文歌唱得不錯,後來還有繼續在學嗎?」
「 馬馬虎虎囉。」 我回答。
阿耀用力往桌子一拍,大聲說道:「 好,那我們上去唱歌,先說好喔,空中補給的不准唱。」 他知道我以前最愛唱AIR SUPPLY的歌。
冷不防,就被他跟大胖拉上舞台去。
深夜兩點多,PUB裡還有不少客人,見我們三人上台,頓時也跟著起鬨。
「 麥可上來打鼓!」 阿耀吆喝著另一名團員上台,回頭又問我:「 臭小子,來條什麼歌?」
「 加州大旅館。」 我將心一橫,直覺就想到最熟的歌。HOTEL CALIFORNIA,是EAGLES唱的世界名曲。
阿耀哈哈一笑:「 這麼芭樂的歌呀?照唱!」
吉他和弦悠悠揚起,他彈奏的是1993年EAGLES世界巡迴演唱的版本,多了許多複雜的指法及大胖那部份的SOLO。看著阿耀不急不徐的彈著吉他,便知道他的功力又不知精進多少。
「 ON THE DARK DESERT HIGHWAY,COOL WIND IN MY HEAD....」
橫豎趁著酒意,我也就放開喉嚨唱了,不知怎地,很快便完全投入。閉著眼抓著麥克風,管他一堆人在看,早已忘情地隨著節奏一路唱下去。
樂音乍歇,如雷掌聲及采聲卻隨即爆開。
阿耀斜眼瞪著我,不可置信地說:「 他媽的,你是我聽過唱這條歌唱得最像最好的,比我們家那個爛主唱還要強太多了。」
我則回以苦笑。
「 喂,會不會『幹您老師』的那條『耐心』啊?我最愛的歌。」阿耀問。
我先是一愣,才意會過來,。
他說的原來是GUNS & ROSES。
「 PATIENCE嗎?應該可以吧。」
「 哇靠,正點!」 阿耀眼裡閃起異采:「 來來來,你給我好好的唱一下。」
他搬來一張凳子,抱著吉他翹起二郎腿,搖頭晃腦彈起了前奏。
PATIENCE 的前奏頗長,第一段彈完時,便要跟著第二段和弦吹口哨。
我見他吹起口哨,腳底打著拍子,漫不經心的表情卻又顯得如此陶醉,不由得又想起他小時的樣子。
真是一點都沒變。
接著我扯開了嗓子唱,原本的味道便是要把聲音唱得沙啞又帶點鼻音,以我刻意模仿的唱法其實是很辛苦的。
尤其到了最後,一句高過一句,高音傳音扯音轉音全用上了,才艱辛地把這首歌唱完,剛好也把嗓子唱破。
好難唱的歌。
采聲掌聲又以數倍響起,阿耀放下吉他,撲過來一把將我抱住。
「 臭小子,我真是愛死你啦!」 他大聲吼叫著。
從此我又跟阿耀,大胖三個人混在一起,連同他們的兩個朋友。
一個是玩爵士鼓的麥可,精壯強悍的光頭;一個是玩KEYBOARD的小蔣,瘦瘦白白又帶點娘娘腔。
後來那間PUB的老闆嫌他們做的音樂太重太吵,要求改善,但阿耀說什麼也不肯,堅持保留自己的風格,只好雙方解了約,一拍兩散。
他們樂團的主唱另謀他途,轉到別的團繼續討生活,其餘的人無所事事,只成天聚在一起玩音樂。
大胖與我,還有鼓手麥可,白天都有正常固定的工作,於是我們大多晚上聚會,直玩到深夜。
阿耀有個怪癖,喜歡開著吉普車,載大家連同樂器,音響,夜半三更到渺無人煙的深山裡去玩音樂,然後吸著大麻,吃著安非他命。
我不明白他愛到荒山野嶺是為了氣氛,還是方便嗑藥,也許兩者都是主因。
阿耀跟小蔣都偏愛這玩意兒,任憑我們其他三人如何勸,怎麼罵,就是死性不改。
我知道他從小就這副臭硬脾氣,天皇老子也拿他沒輒,看著他至少多了幾分開朗活脫,只好也不再勉強勸誡。
「 你懂個屁啊?」 阿耀經常理直氣壯地說:「 大麻、耳環、刺青,這是搖滾樂的基本配備好不好?」 然後捲起他的袖子,指著手臂上史密斯飛船的圖騰刺青。
只是他真的越來越瘦,越不成人樣。
然後他每次都要我和他唱PATIENCE,抱著吉他翹起二郎腿,吹著破破的口哨,搖頭抖腳的一臉陶醉模樣。
我則是每唱完這條歌,肯定破嗓,卻又詏不過他,只好啞著喉嚨照唱。
其實與他們相處一段時間下來,也覺得自己逐漸放開心懷,不似前些日子那樣陰霾,所有的抑鬱悲苦慢慢消散開來,反而有時會覺得過於放浪形骸,像極了時下的年輕小鬼頭。
我從沒擔心過別的,只擔心阿耀的癮越來越重。
他和小蔣嗑藥的次數更見頻繁,用量亦是與日俱增,會開始胡言亂語,行為越見荒誕怪異,我們其他三個人已快看不下去。
我真擔心早晚要發生事情。 |
|
|
|
|
|
|
|
|
|
|
|

樓主 |
發表於 2006-8-1 15:12:13
|
顯示全部樓層
我還記得很清楚,是七月十三號下午四點半多。
那日天空尚且飄著些微細雨,阿耀打電話到我公司來,說晚上八點半大夥兒要一道去深坑的山裡。
我當天適巧疲倦得很,又覺得意興闌珊,於是便推說公司要加班,不能和他們一起去;七點下班遂直接回到中興橋頭的小套房,早早去睡了。
約莫是凌晨兩點多吧,睡夢中被急促的電話聲響吵醒。
我拖起身子有點兒不悅地拿著話筒。
「 誰啊?不知道現在幾點了嗎?」
大胖激動的聲音自電話彼端傳了過來:「 阿文,快點,快到台大醫院來,阿耀出事了!」
郵如晴天打了個霹靂,我完全驚醒。
衣服也沒來得及換,便火速趕至醫院。
阿耀就這麼靜靜地躺在推床上,是那麼地安詳。
我發誓,認識他那麼久,從沒想到如此安詳的表情,會掛在他的臉上。
是不是只有永遠的沉睡了,才能擁有這樣的面容?
阿耀,阿耀。
你一生孤苦,天性桀傲,你就這麼地走,到底對或不對?
看著你削瘦得早已不成人樣的臉龐,你一直都在折磨自己吧?
你笑,我知其悽涼;你癡,我知其愁苦;你狂,我知其悲憤。
你不是要我特地來給你弔唁的吧?
回頭看著淚痕兀自未乾的大胖,麥可,我緩緩開口問:「 誰能告訴我,究竟是怎麼回事?」
麥可遂把事情始末說了出來。
原來下午我推掉了阿耀的深坑夜行之約,大胖與麥可亦也同時有事不能前往,阿耀仍舊帶著同為道友的小蔣,兩人結伴上山。
我們幾個愛嘮叨的人不在,他們也落個耳根清淨,活像餓了三天三夜的餓鬼似地,拼了老命猛呼大麻。
小蔣還沾沾自喜地強調,這次的煙草是西德進口的,藥力強上數倍不止。
阿耀的身體狀況本就越來越糟,這夜早已喝得爛醉,再加上用藥無度,果真出了問題。
而小蔣那時正飄飄欲仙著,只見阿耀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,以為他暈眩醉倒了,也沒有多加理會。
不知過了多久,猛然發現情況不對,這才真的把他嚇壞了。
那時本來還有得救的。
只是小蔣驚慌了起來,不知所措,沒有大哥大又找不到公用電話,更不會開車,只好急急忙忙一路跌撞到山下去求救。
等到救護車來時已然遲了。
死因是心臟麻痺。
我強忍著激動聽麥可說完,才問:「 小蔣呢?」
「 不曉得,應該在外面吧。」 麥可回答。
我點點頭,朝門外走去。
「 阿文。」 麥可拉住我,艱澀地說:「 別為難小蔣,他也很傷心的。」
「 嗯。」 我輕輕掙開他的手,自廊道上一路走出去,便看見小蔣孤伶伶地坐在廊壁的長凳上,仍低頭抽噎著。
他見到我的雙腳立在他身前,抬起頭望來,輕叫了聲:「 阿文哥。」
我一拳便朝他臉上砸去,碰地一聲響。
拎著他領口再將他提了起來,在腹部又追加一拳,然後一腳把他踹倒在地上,連長凳也翻了。
「 我操,再嗑藥啊?嗯?」
「 你以前沒學過急救嗎?心肺復甦你不會?」
「 下山去求救?還是去逃命?」
「 幹!把阿耀的命給我還來!!」
每罵一句,我就揍他一拳,我才發現自己也哽咽了。
小蔣沒有抵抗,沒有還手,只是任我痛毆著。
但我的拳頭卻溼透了,滿沾著我們兩人的淚水。
廊道上已是一片騷動,最後是麥可拉住我的手,大胖自身後抱住我的腰,硬生生扯開我和小蔣。
「 夠了,阿文,夠了。」 大胖的手雖強而有力,卻怎麼樣也止不住顫抖。
「 是阿耀自己要走的,誰也攔他不住。」 大胖口齒不清地說:「 他成天說自己活夠了,沒有半個再活下去的理由,卻有一百個可以死的藉口;還好又再遇到你,他該沒什麼遺憾了。」
麥可也說:「 是啊,不關小蔣的事。」
我又何嘗不知道?但聽到大胖的話,緊握著的拳頭鬆開了,繃住著的身子也癱掉了。
我終於掩面痛哭。
阿耀的走,並沒有驚動太多人。
沒有喪禮,只有在他板橋的家中設了一個小小的靈堂。
阿耀的繼母愁容慘淡,神情憔悴,想必也是傷心過度,畢竟這麼多年相處下來,怎能沒有感情?
我,大胖,麥可,小蔣,四人上完了香,怔怔地望著靈堂上的相片。
又是這副神氣,自小到大看熟也看慣了的,那不可一世的嘴臉。
我將我保存了十年之久的那把他最心愛的吉他,輕輕放在他的靈位旁,這個絕代怪胎,這個蓋世鬼才,讓吉他陪著他走完最後一程。
再也沒人流淚了,我們的淚\都早已流乾。
走出大門,大胖轉過頭來,驚異地看著我,問:「 咦?阿文,你什麼時候去穿了耳洞的?」
我笑笑,並沒說話,大胖隨即露出恍然的表情。
四個人同時停下腳步,不約而同地一齊回頭望向阿耀的家,這時節是酷熱的豔陽天,卻有一陣涼爽的清風,輕輕溫柔地在我們身旁盤旋著。
我知道那是阿耀的不捨,彷彿在對我說著:「 我,只能送你到這兒了。」
再見,我的摯友。
身旁的友人用力拍拍我的肩,再度將我喚回現世。
「 你怎麼了?不要緊吧?」 他好奇地問。
我用手掌將臉上的淚痕抹掉,勉強擠出個笑容,搖頭道:「 沒事。」
看看舞台上那個正在演唱著PATIENCE的年輕主唱,仍搖頭晃腦地吹著間奏口哨,我又不由自主將那個渾蛋的身影與他重疊了起來。
眼前又是一片模糊了。 |
|
|
|
|
|
|
|
|
|
|
|
 發表於 2006-8-1 20:24:16
|
顯示全部樓層
發表於 2006-8-1 20:24:16
|
顯示全部樓層
回復 #3 刀 的帖子
人生的生•離、死•別︿誰能幸免
好文••,好文●●●●●●
把握時間!莫嗟咤光陰★★★★★★★★★★★ |
|
|
|
|
|
|
|
|
|
|
|

樓主 |
發表於 2006-8-3 00:32:39
|
顯示全部樓層
|
|
|
|
|
|
|
|
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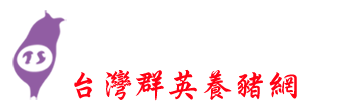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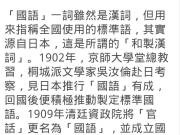
![越南非洲豬瘟疫苗蒙陰影 上百豬隻接種後死亡[轉貼]](data/attachment/block/3e/3e723490e252eebc3bc1a403febd226e.jpg)

![[轉貼]從上市9頭到14頭 -- 我的養豬專業養成之路。](data/attachment/block/3c/3c17fd6b5c1b8cff34fdc7342238e082.jpg)



![[轉貼]這個倒霉王國,因為一隻老鼠慘遭滅國 .....](data/attachment/block/3f/3ffb7b6b8ec14613dc077bdd7603e3a5.jpg)




 IP卡
IP卡 狗仔卡
狗仔卡 發表於 2006-8-1 14:24:11
發表於 2006-8-1 14:24:11
 提升卡
提升卡 置頂卡
置頂卡 沉默卡
沉默卡 喧囂卡
喧囂卡 變色卡
變色卡 搶沙發
搶沙發 千斤頂
千斤頂 顯身卡
顯身卡 樓主
樓主


![越南非洲豬瘟疫苗蒙陰影 上百豬隻接種後死亡[轉貼]](data/attachment/block/d2/d2539d8909b33105a4f3e3b9b2e8a659.jpg)

![[轉貼]從上市9頭到14頭 -- 我的養豬專業養成之路。](data/attachment/block/81/819f9b837f86a7e00498f8d95b8b9176.jpg)

